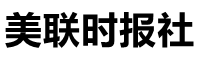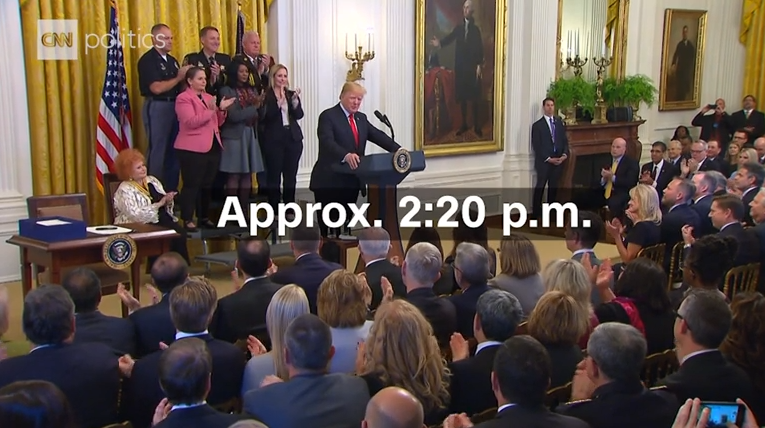本篇文章4385字,读完约11分钟
与其他讨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以及民权和性少数等类似运动的电影和电视剧不同,美国夫人侧重于保守派的反击,他们在20世纪中后期“阻碍”了这场蓬勃发展的社会运动。正如很多后知后觉者指出的,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era)的领袖菲利斯·施劳利(phyllis schlafly)和以家庭主妇为主要成员的组织成功阻止了era被写入宪法,这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一独立事件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菲利斯·施劳利的成功与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发起的保守派的强势回归以及20世纪60年代各种反传统和权利斗争运动的“拨乱反正”密切相关。但由于施劳利反时代行动的意外成功,成为这一保守回归的标志性里程碑。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在六七十年代兴起并蓬勃发展的第二波美国女权运动正式宣告结束。
当制作这部剧的大卫·沃勒(她也是《广告狂人》的制片人)回答为什么菲利斯·施拉夫利是一个“反女权主义”的人物来讲述这段历史时,沃勒提到这件事可以在最初的反时代活动中找到线索,无论是针对当时美国抑郁的保守派,还是后来美国的政治结构,甚至是今天美国的许多问题和争议。美国典型的“反英雄”施劳利在反时代活动中以及她与主流女权运动的摩擦、冲突和斗争中采取了各种立场和言论,这也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反思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弱点及其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和失败。
施劳利反时代的成功与当时美国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有关,但或许更重要的是,女权运动(以及类似的民权和性少数)中的问题导致运动本身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整合力,一方面难以抵御外界保守的社会政治氛围,另一方面自身的衰落也导致运动的势头直线下降。在《美国夫人》中,女权运动领导层内部的模糊性、矛盾性和局限性导致群体内的离心力迅速增大,最终导致原本团结一致的女性群体迅速分裂,最终失去了原有的力量,因此难以抵御咄咄逼人的保守反叛。
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在于女权领袖们在政治上的许多问题和优先事项上的不同观点和分歧,更重要的是,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所建立的基本理论范式的局限性和问题导致了几乎不可避免的分裂。许多评论指出,美国女士女权运动的最终失败实际上是主导第二波女权运动的自由女权主义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Of of Women)为第二波女权运动带来了力量和灵感,格洛丽亚·斯坦纳姆(Gloria steinem)是女权运动的主要发言人,她坚持传统自由主义的女权立场,推动了整个运动的发展。就像当时的其他女权主义思想以及后来对这一思想的讨论和批判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其自身的问题和局限性。
在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问题》第一章中,巴特勒首先对“女性”这一概念提出了质疑,这一概念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中占据核心地位,各种女权主义理论应运而生。在巴特勒看来,“女性”这个本质属性,似乎是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是非常不可靠的,而且由于背后的构建和权力运作的阴影化过程,往往会出现新的划分和排斥。也就是说,当女性主义借鉴传统自由主义关于“人”的普遍性和同一性的思想时,“女性”就成为一个自然的、普遍的本体论范畴,一旦成为现实政治行动中的指导原则,我们就会发现,谁能被视为或符合这样的“女性”标准,往往会充满歧义,甚至被忽视。
质疑这个看似不容置疑的“女性”概念,其实出现在女权运动的第一波。黑人女性代表在参加当时美国主流白人女权运动的会议时,提出质疑——“我不是女人吗?”——直接暴露了这个“女性”主题背后的种种局限。巴特勒指出,以性为基础的“女性”概念,抚平了其他一切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的差异,从而将所有女性按照同一“性别”模板整合起来,最终似乎成为一个人。在《美国夫人》中,这种对女性主义领导权的忽视主要表现在她们对家庭主妇这个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几乎占据绝对数量的群体的忽视、批判和蔑视,以及她们在处理黑人女性的欲望、权利和抱负方面的忽视和局限(这背后也有主流白人的歧视。而很多歧视都是通过一种无意识来揭示的)。
菲利斯·施劳利(Phyllis Schlafly)准确地看到了女权运动概念和实践理论中的这一缺点和局限性,开始动员人口基数巨大的家庭主妇,用她们熟悉的语言和思维逻辑来解释和污名化时代,从而唤起家庭主妇的普遍危机感,维护她们的既得特权(在剧中,她们认为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是一种“特权”,而不是剥削。他们开始组织和行动,最终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施拉夫利完美地指出了男人的弱点,即母亲、妻子和女儿——家庭中的“监护人”——的某种秘密耻辱)。
对于贝蒂·弗里丹或其他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来说,这些家庭主妇之所以看不到父权制和家庭对她们的剥削和压制,完全是因为她们的无知、顺从和不愿挣脱枷锁。但事实不止于此,因为如果只站在“女性”的立场,家庭主妇难免会遇到传统宗法制度的种种限制,但一旦从阶级、社会地位等范畴来看,事情马上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在像Schlafly这样的白人中产家庭主妇眼里,生活中的很多不平等或差异不是来自性别,而是来自其他原因。在Schlafly和betty friedan的辩论中,前者解释说女性找不到丈夫是女性自身的问题,并指出女权运动将其归咎于性别不平等显然是错误的。(Schlafly很会用修辞。在她的许多陈述和判断中,我们经常发现真理和谬误并存。由于她对听众心理的准确把握,她可以通过夸大和耸人听闻的谬误成功地引起听众的焦虑和恐惧,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使人们忽略她话语中的许多谬误甚至荒谬。(
李非与凯特·布兰切特
女权运动是否应该包括或争取家庭主妇的争议,以及对黑人女性或女同性恋少数群体的利益和欲望的忽视甚至排斥,也直接引起了对看似普遍的“女性”概念的质疑,产生了新的内部分歧。正是随着“差异”概念的出现,离心力在女权运动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美国夫人》中,有几个片段提到贝蒂·弗里丹对女同性恋者的排斥,认为她们在女权运动中处于劣势,并称之为“薰衣草的威胁”。美剧《当我们崛起》中,那个满怀期待的女孩参加了现在由弗里丹创立的美国全国妇女组织,却因为是同性恋而被拒。最后,她去洛杉矶成立了一个属于女同性恋团体的组织,从而开始了自己的运动。这种遭遇也发生在黑人女性身上,所以在《美国夫人》中,她们也开始分开,建立自己的组织,关注自己的问题和各种困难。
这种被福柯称为“身份政治”的社会运动模式在美国六七十年代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使原本处于社会边缘和主流的少数群体开始走上舞台,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另一方面,它也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和局限性,那就是因为大多数都是基于一个越来越被认为是本质的身份(无论是女性、黑人女性、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等等)。),他们在争取解放的同时,也为自己画了一座监狱,又因为差异可以无限探索,原本注重的普遍性和共识性逐渐被抛弃,难以形成团结互助。最终,群体继续像细胞一样分裂,削弱了他们面对强势回归保守势力的能力。
除了20世纪60、70年代各种群体为了自身“特殊”的欲望所反映出来的直接经验和实践外,还与那个时期兴起的整个哲学转向有一定的联系,特别是各种“后研究”的出现,使得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被视为典范的理性及其关联的普遍性、同一性、主体等概念受到质疑,从而开启了对各种差异的关注。福柯在评价美国六七十年代的同性恋运动时发现,基于“差异”性取向的身份政治开始成为少数群体争取自身权益的典型手段。尽管福柯对此仍持怀疑态度,但他仍然无法阻止这一趋势成为主流并持续到今天(lgbtq……)。
正是因为巴特勒对基于身份的传统“女性”概念的批判,一些美国学者,如努斯鲍姆的《戏仿教授》,批评巴特勒对女性差异的强调,最终可能导致主体在真正的政治运动中失败,从而导致运动的失败。根据《美国夫人》的介绍,努斯鲍姆的批评不无道理。正是因为对“差异”的重视,女性迅速分化,也正是因为对“差异”的过度崇拜和迷恋,使得每一个群体都因傲慢或意见分歧而与其他群体疏远,一方面使他们无法相互理解,另一方面也难以形成联合的政治行动,最终导致在面对对手时节节败退。
这个可能是分化造成的问题,从70年代开始就被这些群体注意到了。因此,在《当我们崛起》中,性少数群体也强调他们对黑人民权、工人阶级抗议和反越战等其他运动的参与和互助。在英国电影《2017年的骄傲》中,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时期英国矿工抗议的时候。一些同性恋组织希望帮助矿工,通过各种渠道与他们沟通,帮助他们筹集资金,协助物资。这种放下刻板印象而形成的友谊,最终让矿工团体需要同性恋团体的帮助。能积极互助...
在李察·沃信的《非理性诱惑》一书中,作者批判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于法国的各种后学派(学院派左派)在质疑甚至抛弃西方传统哲学和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理性、民主、普遍性等基本原则时形成的反理性、相对主义甚至文化种族主义。在沃林看来,正是由于他们对“差异”的过度尊重,使得基于他们的各种社会观念或运动趋向于自我限制,从而导致某种不可避免的绝对性和不宽容性。但是,当原本作为民主社会基础的共识被忽视时,就会直接导致联盟越来越困难,最终失去对抗破碎小团体中强大保守势力的能力。而且这在美国社会不常见吗?
如果《美国夫人》的这段话能够启发上世纪末女权运动失败的历史中的当下,其中之一可能就是如何重新连接。随着反性骚扰和性侵犯运动的诞生,我们也发现新的联合企图开始重新出现。事实上,无论是巴特勒对“女性”这一本质概念的怀疑,还是努斯鲍姆对“女性”这一概念的解构所引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担忧,都是为了解决一个结构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女权运动中,也存在于其他许多基于某种性质(从而形成差异)的身份政治中,即如何一方面保证群体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又不抹杀群体内部的差异。
而这个问题,远不仅仅是美国或者西方面对这样的运动,其实也和我们遇到的现状息息相关。一方面,在各种身份或差异中建立基础的诉求有其合法性,但另一方面,也受到弱小、难以抵抗的强大反对力量的威胁,也可能导致被他们一个个吞噬的结果。因此,如何在共同的基础上或共识上形成团结,也许是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紧迫任务。因为就像《当我们崛起》里的主角说的“同样的奋斗,同样的奋斗”,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别人怎么做可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朋友怎么做。(本文来自《The Paper》,更多原创信息请下载《The Paper》app)新闻推荐
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达到298.1万,高于预期
美国劳工部5月14日数据显示,美国5月3日至5月9日这一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298.1万人,此前数值为316.9万人,预计人数为250万人。据报道,美国周信...